“咔嚓——呼”一声尖响一阵寒风骤雨灌进车厢,沉闷拥挤的车厢前排那块已有裂纹的玻璃窗,在公共汽车急转弯中被震飞了大半块。一阵忙乱之后,就听见乘客中有人说:“大清早就遇这样的霉头!”“唉,现在乘车,真是……”后面那位留着童式短发的年轻女售票员红着脸,一声不吭地站起来,走到破玻璃跟前。看见座位上一对盲人夫妇手握着手,默默地坐着,雨水已经打在他俩的脸上和衣服上。姑娘的脸更红了,忙撑开手中的花折伞,堵住窗口。

车厢里一下子静了,大家向姑娘投去敬佩的目光。
“对不起,乘客们。这块玻璃应该换了。怪我们……”姑娘的话刚说了一半,一股急风把她那娇小的身子刮退了半步,话也咽了进去。这时,一只大手抓住伞柄,助她往前一顶,只听“噬——”伞面被尖利的`玻璃划了一道口子,伞骨也断了一根,但洞口又封住了。姑娘朝着身边这个40多岁、面带歉意的大汉感激地笑了。
“你去吧,我来。”大汉胸前的红字表明他是一个钢铁工人,他的声音就像钢铁一样坚强有力。
姑娘又忙着招呼售票,声音比原来更甜更亮。
“玻璃窗修好了?”盲人夫妇问。
“修好了。”大汉神气地回答。
“那就好。”
乘客们都会意地笑了。车厢里显得格外温暖。
公共汽车又过了两站,大汉旁边的一位正在背外语的小伙子突然伸出手来:“你休息一下,交给我吧。”“好!哈哈……”
一站接一站,一人接一人,伞柄被人们捏得暖烘烘的。这上面的暖意不断传给接伞的后继者,同时也传到了每一个人的心里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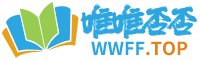
 粤公网安备 440106xxx4424
粤公网安备 440106xxx4424